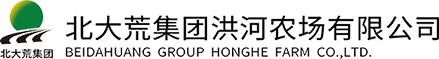秋收时节,我站在洪河农场的田埂上,眼前便是一片无垠的金色海洋。那沉甸甸的稻穗,密密地挨着,汇成一片庄严而温厚的辉煌。风是有的,却似乎撼不动这饱满的谦逊,只惹得层层的浪,从天的这头,悄无声息地滚到天的那头。这寂静,是暴风雨前来临前的那种寂静,蕴藏着一种即将喷薄而出的、巨大的生命喧响。这景象,本应是千年不变的,可你若细听,那喧响已不是四十五年前镰刀的轻吟,而是另一种更为雄浑的节奏,正从天边沉沉地传来。
看呐,那庞然大物来了!是一台联合收割机,像一艘威严的金属航船,正破开金黄的浪。它的履带碾过田垄,发出坚实而钝重的声响,仿佛大地沉稳的心跳。那前端的割台,张着巨口,如饥似渴地吞没着排排稻禾。这“吞”却不是毁灭,而是一种奇妙的点化。稻秆被齐整地切断,卷入它那复杂的腹腔;霎时间,只见金色的谷粒,如同欢快的瀑布,从一旁的“巨臂”中倾泻进紧随其后的卡车里;而那被梳理得干干净净的秸秆,则从后方吐出,均匀地铺洒在土地上,成了一条条软塌塌的、带着清香的金黄色毯子。
这真是一首钢铁与稻禾合奏的、雄壮而又精细的韵律诗!一吞,一吐,之间便是洪河农场六十多万亩土地的收获。我想起古画里那“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的场景,那弯腰如弓的脊背,那挥汗如雨的臂膀,那镰刀划过禾秆的“唰唰”声,虽是诗,却浸着劳作的苦涩。而今,这苦涩大抵是被这机械的伟力涤荡去了。人,只需悠闲地立于田头,像将军检阅他的士兵,看着这铁马金戈,为他完成这世代最艰辛的战役。效率,这个词从未像此刻这般,具象为一种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轰鸣与流动,感慨现代化大农业、打机械带来的酣畅。
我的思绪便不由得飘忽起来。我想,千百年来,滋养着我们这古老民族的,便是这土地与躬身的农人。农人与土地,面对着面,几乎是贴着胸膛的厮磨,汗水直接滴入泥土,情感也便深深种了下去。那种联系,是温存的,是带着体温的,像母子般的脐带相连。而今,人站远了,他与土地之间,隔了这层冰冷而高效的钢铁。这机器,是个忠仆,却也是个隔膜。它不懂得一株稻禾在微风中的摇曳是何等美丽,也体会不到掌心被禾叶划过的微痛。它只是精确地、忠实地履行着指令,将丰收变作一道纯粹的工业流程。
夕阳西下,给这金属的巨兽和广袤的田野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玫瑰金。收割机完成了它的工作,静静地停在田中央,像一个疲倦了的巨人,周身散发着温热的气息。卡车满载着金灿灿的谷粒,缓缓驶向远方。空气中,弥漫着新谷的醇香和柴油那特殊的气味,这两种味道交织在一起,便是这个现代化农场特有的、矛盾的丰收气息了。
我转身离去,身后的田野安宁而空旷。那铁马的轰鸣犹在耳畔回响,而那千百年来无数个沉默的、弯腰的背影,也仿佛在记忆的深处,凝成了一首无声的、古老的歌。现代的歌谣固然嘹亮,而那古老的余韵,却总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低回不已。这,便是进步的代价,抑或是它必须承载的、甜蜜的哀伤。 (谭心)